对于六岁以前的事,我全然没有了记忆。只是从我的父母口中得知,我是一个把双脚穿进一个裤筒,摔倒在地上不哭也不喊的“傻孩子”;看见别人吸烟很好玩,背着大人偷偷的捡别人丢弃的烟头,自己躲到一边“享受”,结果染上甲肝的“坏孩子”;身上长了毒疮,看见了医生就大闹,宁可自己受罪也绝不去医院治疗的“呆孩子”……所有的这些,现在早已是父母闲暇时的笑谈,而我现在听了也只是置之一笑。
在这以前我是快乐的,但改变现状的事却往往发生在突如其来的瞬间。
那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六用的天,很热,天上没有云,蓝的刺眼,太阳很烈,有种眩目的感觉。在老家屋后的山坡上,我和劳作的父母在一起,谁也不知道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会民生什么,一切都是未知的,没有任何征兆。
在离我较远的地方滑下一块石头,机警的我本能的跑开了。其实不用跑的,石头离我很远,不管怎样是不会伤到我。而我这一跑,却和命运开了个很大玩的笑——我被一根小树桩绊倒了,这一倒便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我倒地上,哭着,撕心裂肺的喊疼。父母丢下手中的活心急如焚的抱起我把我送到村卫生所,医生看着我那肿起的腿说:“很可能是骨折了,快送人民医院!”当醒来时,我已经躺在四壁洁白的病房里。院方通知我父亲:我需要手术治疗并且速交医疗费。父亲在最短的时间里凑足了钱,用颤抖的手在手术协议上签了字。
第二天上午我就要做手术,从进院到手术前,我没有吃半点东西。疼痛也已经麻痹了我的右腿,在失去知觉中我觉得好像好了不少。而现实永远比感观要复杂的多!
第二天早上,在注射科注射了麻药之后,几个护士把我推进了手术室。那时我还处于半清醒状态,印象中依稀记得医生把我抬到手术台上,往我身上盖了一层白布,然后就在我头上调整一个大圆盘状的灯。刹那间我心中有一股莫名的害怕,但我已没有意志去支配自己去用一丁点的气力喊叫了,再然后我就沉沉的睡了过去。
手术过后,麻药的效用渐渐失去作用,那种疼痛开始在我身上肆意泛滥,我没有掉半滴眼泪,即使再难以忍受我也只是小声呻吟几下。因为我不想让已是揪心的父母再为我感到酸楚。
我开始佩服我眼前我这个人,在巨大的变故面前,他那紧闭的嘴角,滚动的喉结正是一种坚强。他扭过头,望望远处,眉宇间闪现着一丝忧郁的痕迹。或许他现在已把自己置生于曾经的磨难中去了,也或许他在思考着他人生中的每一步,也或许他正感受着一种沉重。“我不相信宿命说,但我却无法摆脱命运的捉弄!”他淡淡的说。
我在床上躺了四个月后,可以下床慢慢的行动了。我以为自己再也不会进入充满刺激性气味的病房和恐怖的手术室了,但随即而来的是我再次进了医院—-我体内还有一块用来固定用的钢板,需要再次手术取出。可复查结果却令人心寒:螺丝松动,钢板离位,接骨处畸形吻合。面对这一切,我和家人却还不知道这还只是刚刚开始我的厄运。在此后的漫长治疗过程中,结果一次比一次差,我开始怀疑我自己是不是走上了一条治疗的“不归路”。
在医院的那段时间,其它科室的医生经过我的病房时,总会带着关切进来看看我的病情,然后却摇着头走出病房。在他们眼中,我的这点伤是很容易治好的,而现在却在我的主治医生下,治疗结果一次比一次坏,这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也在为我惋惜。
有时候我也觉得我自己还是经得起磨难的,不过这些都是建立在不幸与痛苦之上的。我所经历的每一过程,我现在都还感到后怕,在我心里这是一条划得很深很深的伤痕,那些治疗方法无疑都是变种的“刑法”。
我的整条右腿打了石膏。整条腿被包裹在里面,有知觉,但却没有丝毫动的权力。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密不透气,里面全是一股闷臭,长时间不能擦洗,瘙痒袭来时,犹如万蚁啃食,我真的快不能忍受了。当我无法用忍受来安慰自己时,我就用手使劲的在坚硬的石膏上按压,哪怕有里面有一点点和皮肤接触的感觉,也是一种难得的舒适,或者说是种奢求。
后来为了拉直腿,我睡在头低脚高的床上,整条腿放在吊架上,下面系着三块红砖,和我的腿相连。时间长了,我右脚踝处磨出了厚厚的茧,还有暗红的血泡。由于长时间这样吊着,没有了运动,我的右膝盖失去了正常的机能——已经完全不能正常的弯曲。我又忍着阵阵揪心的疼痛锻炼我的右膝关节,因为我还是奢望着有一天能像正常人一样飞一般的跑!
再后来,在上钢板不能固定的情况下,又用20多公分长的钢针从骨中心穿过,希望能完好的固定断骨。可这种方法却没有达到预期中的效果,由于定位不准,再次离位!这一次,我的伤口也感染了,脓和血水染污了洁白的床单。伤口久医不愈,腐肉已经有了恶臭,不得已之下,医生剜去了累生的腐肉。。。。。。
在近四年的医治过程中,我共做了六次手术,每次都是全身麻醉。别人说全身麻醉多了,会对人的中枢神经有影响,智力也会比正常情况下低。可现在我发现我还没有完全笨到家,照样在读大学!
每一次手术,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坎,并且这个坎一次比一次高,一次比一次艰难。穿梭在这条命运线上,有时真不知道自己是在“挣扎”还是在“抗争”,或许我只是以一种低调的人生态度平静的面对着这一切变故吧!何况在很大程度上为了一个“奢望”,我没有选择,只有顺从!相反,对面那些大大小小的针管仪器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我也习惯了,每次我被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心中更是一种无奈的安然。所有的一切我都经受了,也挺过来了,再多这一次对于我来说又算得了什么?
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腿始终没有医治好。适得其反的是我的腿由于过度频繁手术,早已经停止了生长,肌肉也萎缩了。最后的结果是:我成了三级残疾!
尽管他讲的都是他的忧伤往事,但他却坦然的对我一一道来,没有掩饰,也没有悲怜,对往事仿佛已经淡化如水了,和常人一样过着平淡却又充实的生活.“你有过悔或是恨吗?”我这样问他。他抿嘴笑笑,“恨?恨不能改变现实!而爱却能包容一切!在那段不愿回忆的日子里,有我的父母在为我奔波,有我的奶奶在悉心照顾我,还有我的很多亲朋好友在关心我。我并不孤单无助,因为有他们!”
在医院里的大部分时间是我的奶奶在照顾我。奶奶天天都守在我的床边,晚上也是和我睡一起。病房里的床和现在宿舍里的床一般大小,我躺在上面已经占了绝大部分,在晚上,奶奶要睡的话就只能蜷缩在床的一角,她要尽量占用少的地方,以免触到我的伤腿、影响我的休息。有好吃的,奶奶总是以各种理由推托说自己不吃,哪怕是放在那儿烂了她自己也舍不得吃。我现在责备自己那时没来得及说一句“谢谢”,以至现在已经永远没有机会再说了。
也就是在那种“日出在床,日落也在床”的无聊日子中我度过了难熬的一天又一天,并且和我的奶奶在医院里度过了两个春节。本该是万家团圆的日子,而我和奶奶却在孤寂的病房里守望着窗外黑暗中潜伏的新年。尽管好吃好喝的都摆在我的床前,但在那种情况下决然是没有胃口去吃了。哪怕是寒风凛冽,我总是固执的坚持叫奶奶把窗子打开,看着除夕的夜空下时时闪现的礼花,想着自己什么时候能活蹦乱跳的在自家门前开心的燃放烟火就成了我唯一的愿望,甚至我认识那就是我的理想。当窗外的人们全沉浸在喜悦中时,而我却在病房里默默的观望。。。。。。
我的父母也在家和医院之间不停的穿梭。他们仿佛在一夜之间老了许多。为了我,他们在没日没夜的劳作,挣钱给我治病成了家中的头等大事。但身处农村的我们,在经济上并不宽裕,家中的老底已经用完,在亲朋好友中能借的钱已经借了,家中除了累累的负债已经没有什么了,也就是说,为了我,家中已是到了一穷二白的境地了。我知道父母不想让他们心中的希望就这样生活在痛苦的阴险影里。父母流过泪,是为我,我看在眼里,却无法用某种语言来安慰父母,其实我明白父母,但是我却不明白在贫穷的情况下我还有没有完全康复的可能!
到现在我还很愧疚,因为为了我一个人,却苦了我一家。这些如果说要偿还的话,我真不知道拿什么去偿还给我的父母和奶奶!他们为我付出了太多太多,我要偿清的也太多太多。当我在医院吃着热腾腾的鱼和肉时,我的家人却在家里吃着最清寒的粗茶淡饭;当我在床上睡得正憨时,我的父母却在田间地头披星戴月的干活;当我用钱买来我喜欢看的书来尽情享受时,我的家人却握着手中仅有钱在考虑怎么去用。我现在才渐渐明白,我的父母是在用花白的头发和深深的皱纹给我构筑着一个足以弥补我伤痛的爱巢。
由于我在医院耽搁了很长时间,我的学业也耽误了两年。是父亲在床头给我买来书和学习资料供我学习用。可以说我的学业是断断续续的完成的。在初中和高中,我也遇到并认识了很多的好老师和同学,他们在生活中和学习上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关心。现在我有所明白,当一个人失去了一些弥足珍贵的东西时,在无形中却又得到了很多其它的宝贵的财富。
“你知道吗,我从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残疾人来看。我不否认自己在身理上有无法弥补的缺陷,但我要说我并比比正常人差多少!从实质上讲,我只是比比正常人多了一些不方便而已!”听着他自信的声音,我看到了一种精神在跳跃,火一般的跳跃!他缓缓说道:“我喜欢一句话,大致意思是这样的:‘忧患是一种沉重而痛苦的清醒,我宁愿选择一种痛苦的清醒,也不愿活在麻醉了的冷漠之中。因为,忧患的痛苦是为了更多的不痛’。这句话也许说的太沧桑了,但我却折服于它。”
最后一次手术后,我和我的父母面对了现状:既然无法完全医治好我的腿,那也就只好承认现实。
我出院了。在出院之前,还欠医院几千元钱。父亲心一横,没有交清欠费就把我抬出了医院,医院愧于自己的职责也没有追究什么,好像一切都很平淡,但又有谁知道这种平淡之下是怎样的一种心酸。
而后,我拄着拐杖上学了,有两年的时间我是拄着拐杖在学校和家里往返。那时我还真有点担心能不能扔掉拐杖,有自己的双腿慢慢去上学,哪怕是一跛一跛的。在学校里,我总是以一种最积极的态度对待着一切。我凭自己的本事争得到的荣誉成了我展示自己的资本。在我的同学当中,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我是一个有能力有魄力的人,在他们的认同之下我当了班长。现在想想,我做了那么多年的班长好像还不知足,进了大学还继续赖着不下台,有尸位素餐之嫌。
在去年暑假,我参加了宜昌市的残疾人运动会,由于我是一个在江边长大的孩子,顺理成章的拿了游泳项目的第二名,并顺利入围了2006年的湖北省残疾人运动会。同是在那一个月,我收到了三峡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喜悦上了眉梢,那一年,我笑的最甜!
当他讲到自己的成就时,甜甜的笑了。从他所遇到的一切中,我发现磨难并不会消磨一个意志,特别是对于这样一个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经历的人。有人说,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可我要说,无法承受重量的生命是不堪一击的生命。或许在我们身边,还有比他身世更难以想象的人,但他们也许活得很开心,同样的在为自己的生命寻找着一根支柱,困为生命可贵,人生的路还远。他一个人的事并不难包揽所有,但从一个侧面我们可以管中窥豹:命运的不公不应该埋没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清楚,究竟应该怎样选择,怎样面对,怎样拼搏!
坚强的走过,才显生命真风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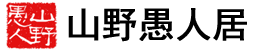
 用支付宝打我
用支付宝打我 用微信打我
用微信打我
都没什么。看,已经被你踩在脚下了。You are strong。
一字一句的认真看完了,莫名的感动了,好长时间没被感动了。认得你应该也有六年多了,我们一直不咸不淡的交往着,这六年,我很少想到过你的腿脚不方便,因为我一直把你当做一个健康的人,确实你在大家眼里也就是这样一个人。很少信服别人,不过你是例外,因为你比我强一大截,我没有理由不佩服你。生活会很艰辛,相信你会一如继往的给大家做好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