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小姐。霉鬼。”一小孩靠过来如是说。
顺着只能用脏来表述其特征的衣服向上看去,一双眼睛在狡黠中透出与其年龄不相符的世故,孩童最美好的真纯被掩藏在了滔滔不绝的死缠烂打之后,或者已在不经意间褪去,他们自己也无从察觉,任其流逝。
笔者曾向其中一个卖花的小孩问到是否在上学,他眨眨眼睛,说他卖花是在为自己挣学费,当笔者继续追问他出来卖花父母是否同意,或是有人指使时,他见笔者无意买花,丢下一句“bye-bye”,跑开了。
夷陵广场、滨江公园,总之是在稍能代表城市形象、较雅致的地方,总少不了这样一些声音,一群身影。虽然近来经过有关整顿,但如上所述的变相形式乞讨仍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此风景虽然与都市的物象看上去那么格格不入,却是哪个大都市都赶不起走的一个特殊群落,这个群落无所不在,大致划分来,可总结为传统型、优雅型、耍赖型三种,分别表现如下:
传统型:一纸凭书,书不尽满腔血泪,或孤苦无依,或被骗来**,人则默坐不语,跪守一旁。
优雅型:广场前的人行隧道里,一名男子头戴鸭舌帽,不仅相貌不凡,而且衣着不俗,抱一把吉他唱得感情澎湃,若不是面前的盒子里撒满钱币,谁也不会想到他是乞讨者。
耍赖型:当然非那些强行抱脚卖花者莫属。在人流汹涌的街市,时不时可以看见一些儿童,手拿一束玫瑰花追着人跑。逢节假日尤甚,而且更加肆无忌惮。
就是这样一群人,被社会学家称为最边缘化的群体之一。他们无家可归,躲在地铁里又刺眼又刺鼻,行人见之,哀其不幸者少,怒其不争者多。
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社会贫富迅速扩大,大批乞丐的出现正是这种趋势的副产品;与此同时,乞丐数量的增加也是去年中国人权状况改善带来的出人意料的结果。
目前我国的乞丐大有组织化倾向,即许多乞讨行为已经不是个人行为。在一些丐帮头目的控制下,许多未成年人被组织利用,作为强行索要的主体,划地结伙,突破了宪法赋予行乞者的权限,对秩序和治安构成威胁。
在《信息时报》1月6号报道的宫璇璇事件中,12岁的残疾女童宫璇璇成为这一类典型犯罪的受害者。乞丐头目毫无人性地割伤她的大腿,然后逼迫她用淋淋的血作为伤口赚取路人的怜悯。
这一报道公诸于众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的震动。犯罪学家李斯特说过大众的贫穷是孕育犯罪的的最大基础。虽然贫穷不是这些“乞讨犯罪”的辩护理由,但却是生养这些犯罪的土壤。因为贫穷,很多人不得不乞讨为生,而“乞讨犯罪”现象正是籍此孳生。
流浪的人群各有各的不幸。部分农民因为被剪刀差剪去的资源太多了,迫于贫困需要到城里来流浪乞讨。而下岗职工则是另一股近年来崛起的,在数量上不容低估的流浪人群。城市流浪正成为一个社会性问题,不容回避而必须解决。
因为贫穷而犯罪,因为犯罪而必须治理,除“执法必严”外,根本还在改良这片土壤。李斯特说改善底层生存状况是最好和最有效的刑事政策。
面临日益增多的城市乞丐和由此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一些城管部门尝试设立了“限制乞讨区”,由此而在社会上引发了一场关于乞丐人权的讨论。《新京报》对此发表评论说“对于城市乞讨问题,中国社会应该有一个讨论”,而要负责地看待这一讨论,首先得看清对这个问题的基本价值判断是什么。
在英国工业革命初期,大批农民沦为“流浪汉”。英国政府把他们关进“习艺所”,在酷刑下强迫劳动。这种过激的政策受到了人权卫士的强烈批评,并导致了以后在限制人身自由方面逐渐宽松,“济贫法”和“新济贫法”相继出台,最终演变成为以人权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救助制度。但是,在这整个变化过程中,“不养懒汉” 是不变的基本价值判断。
笔者对于设立“限制乞讨区”的做法还是表示理解,最起码该治理行动还体现着对乞丐的人身权利的尊重,因为既然有“限制乞讨区”,自然也有“非限制乞讨区”,它并没有剥夺个人在困难的时候有乞讨的权利。从人权上来说,乞讨,卖艺不应被禁止,但这并不排斥从善治的角度进行人性化的管理。
人们以密集的言语,就乞丐问题表达着自己的人权观。占优势的是主张乞讨权的一方,他们的一个重要理由便是保障人权首先要保障生存权,特别是弱者的生存权。
与此同时,4月1日的《南方周末》上登出了一篇题为《乞讨权是一种什么权》的文章,发出的是另一种声音,文中表示最核心的问题是“到底是应该为乞丐争取做人的权利还是为他们争取做乞丐的权利,到底是应该为乞丐争取乞讨的权利还是为他们争取不乞讨的权利?”文章观点认为乞讨权只能把那些安于乞讨的还原成苟且延生的生物。因此关键的不是争取乞讨的权利,而是要争取不乞讨的权利,由国家宏观调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纳乞丐于正常的社会生活之中。
这个意见在理论上当然是不错的,只是若要付诸实践,有两个事实还必须置于考虑之中:
其一,当前中国正面临的是“总量性失业”,劳力相对过盛,无论怎样发展生产、经济,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劳动力市场上供大于求的矛盾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
其二,在乞讨人员中,除少数是迫于一时之急不得已而为之外,大量的是“职业乞讨者”,如老年人、残疾人,他们原本没有劳动力,所以“提供就业岗位”对他们根本无效。另有一群人是有劳动力的,他们不是因为没有就业岗位向人伸手,而是自愿选择了乞讨为生的生活方式(如安徽的“瘫子村”),这就是在中国文化中被视为“懒汉”的一种典型,“提供就业”对他们显然也不合适。
乞丐起源于人类贫富分化之肇始,游离于社会活动之边缘,与主流的不和谐由来已久。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这样一个群体正象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套用一句官话,流浪乞丐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繁盛阶段,并且现实的生存环境也决定了这个历史渊源深厚的名词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失。有社会学家称主流对边缘能够包容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全社会的宽容精神和实力。
流浪下去没有未来。在这样一个处处寻找“人权”的时代,这个词正在泛滥,而真正需要人权来关注的这么一群人却绝少能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尽管有许多人在为他们呼唤,他们却懵然无知。
叔本华说人的满足是没有止境的,但在一个只有最低限生存要求的人眼里,他们要求的是什么满足呢?正如一句话所说的,乞丐只会去嫉妒比自己多讨了一块面包的乞丐,而不是去嫉妒百万富翁,在他们为了一块面包而欣喜的时候,他们还会去奢求选举权或被选举权么?在他们选择(或被迫选择)这一生活方式的同时,许多权利都在事实上失去了。
还是回过来再看那些卖花的小孩,他们正值—-之年,他们的世界本应该是快乐无忧而充满幻想的,结果却在某些人的控制下过早地闯入这悲惨世界。不管卖花是否他们所愿,小孩是无知的,他们不应该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剥夺了选择人生的权利,他们也葆有“受教育权”,但是这种权利何时在他们身上真正得到履行?
这一群人!他们的未来在物竞天择的现实社会中将何去?何从?如果他们还有下一代,边缘的命运或许还要代代相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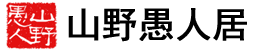
 用支付宝打我
用支付宝打我 用微信打我
用微信打我
发表评论